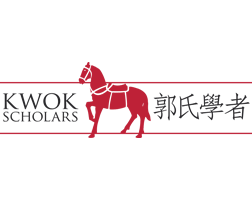12 June 2023
12 June 2023 

By Brian Wong
我在牛津這八年(二):我的未來不是夢
此時此刻的禮堂中,除了間歇性的喝水聲與初夏的窗外鳥兒叫聲,基本上寂靜無聲。這是一個不可侵犯的聖地。這裏也是噩夢與美夢交織之地。坐在椅子上,手不停而眼不移的芸芸學子,正嘗試在時限前達成目標,將一點一滴能榨出來的論點狠狠地寫下來,寄望考官能在批卷時「高抬貴手」,施予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成績。
這是牛津大學考試大堂(Examination Schools)每年4月至6月司空見慣的場面。數百名出類拔萃的學生,按序地排隊進入這座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學院重地,然後在裏面面對着他們的,則是也許他們一生人裏面最為高壓的難關:終考(Finals Examinations),也即是末期試。
牛津(劍橋很大程度如是)與英美其他一般頂尖大學數個不同之處,其一必然是其獨特的考試制度。相對於較為重視每一學期整體分數(GPA)或以每一期期末考試為評分基礎再作綜合評分的院校,牛津最為「殘酷」之處便是,畢業榮譽的主要(甚至唯一)評核基礎,往往乃是在兩到三個星期內便考完的「終考」成績。這一特徵尤以筆者修讀的哲學、政治與經濟(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PPE)為甚。
無論在大學一年級年末的「初考」還是二至三年級間的無數場「模擬考試」(Collection Exams)中的成績多麼出色,若PPE學生在「終考」中達不到標,滿足不了一級榮譽的最低門檻,頂多只能以二級榮譽(上)畢業。當然,能在牛津大學拿到二級榮譽(上),有不少也絕非池中物,但始終主觀與外界觀感上,還是會令人產生與一級榮譽之間的「區別之分」。誠然,這可以說是一種固執,也是間接印證着如桑德爾(Michael Sandel)與項飆兩年前一次對話所指,現代社會透過學術成績的分類,為不同社會階層內部內捲性地塑造「區分」(Distinction)的狂熱趨勢。三年苦功,在三個星期,以分開的八份考卷,每份考卷3小時,共24個小時內手寫完成的24篇論文定生死。這就是當年我和一眾同學必須承受的「木人巷」,這樣「走過來」的。
2018年,我有幸以全級第九名畢業(當然,事實證明,考試「很出色」與人生閱歷或最終成就是沒有太多掛鈎的),當然感到一定的自豪。還記得「終考」的同時,我正在協助一位同在終考的朋友競爭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主席職位──最終其以些微票數落敗,但雖敗猶榮。每一場考試之間都安排了與朋友團隊的一眾候選人見面,結果自然是忙得不可開交。現在回想起來,卻對那段時光充滿懷緬與嚮往……
擁有九百年歷史的牛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新冠疫情與學習電子化以後,牛津終於將部分考試從手寫改成以電腦輸入,甚至有部分科目以「開放考試」(open-book examination)取代那嚴苛非常的「封閉考試」(closed-book examination)──學生可以自帶筆記與書籍去應試。這些改變,無疑讓考生壓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紓緩,卻也變相篩走了部分本能讓考生相互之間作出區分的比較範疇(例如記憶力、複習時紀律等)。
2023年,走在牛津街頭上的我,看着穿戴着紅白花朵(紅花象徵着赴考最後一場考試,白花為第一場考試)的本科生,心中不禁激動起來。年輕,真好。
一、 進入牛津:是我選擇了牛津,還是命運選擇了我?
小時候,我的志願是要當一名大律師。Suits與《怒火街頭》等電視劇當中,大狀主角永遠都是正氣凜然,不會單純為了政治或經濟酬勞而折腰,更不會屈服於強權與威逼利誘之下(黃子華《毒舌大狀》,我看了兩遍)。現在聽起來可能覺得有點天真(但我依然對世界各地從事法律工作者抱有無比的尊重,因為他們乃是守護公民社會與平民百姓的重要把關者),但這確實是我中一到中四時候的打算。同時,「牛津」、「劍橋」這些名字,對於我這個在香港長大的小伙子來說既陌生,也難以理解。
後來發生了兩大轉變。第一,香港2012至2014年之間發生的種種風波,讓我領悟到,若要批評與改進我心目中認為是不合理而有違道義的行為,必須從更廣闊的哲學與政治科學視角入手,不能單純以「法」為基礎,否則只會墮入循環論證的圈套之中。第二,筆者中學有幾位啟蒙老師,在我感到迷茫非常之時給予了我道德勇氣,灌輸了一個很關鍵、而至今我依然相信的人生哲學觀:「你不嘗試,就肯定會失敗。你嘗試後失敗,那也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啊!」就是這樣,我在2014年盲打莽撞的申請了牛津,並抱着「這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去英國,所以倒不如見識見識」的心態踏上了尋找他鄉故事的征途,與陪伴着我的家人一同來到了牛津面試……
面試過程並非一帆風順。還記得在第一選擇的學院中面試時,我因水土不服而發燒,結果在數輪追問下,變得語無倫次。幸好可能面試官們念在我長途跋涉,也覺得孺子並非不可教也,將我「推薦」至另一所學院(也即是後來考入的彭布羅克書院,Pembroke College)。翌日狀態稍微恢復後,我還記得在經濟面試中,我被邀請估算在兩個小鎮之間所設置的小攤檔,究竟客流與離小鎮距離的關係為何,從而推理出一個可行的收益函數。政治面試,則被要求就着暴力的合理使用提出一個論證框架。本來嘗試「面面俱圓」地蒙混過關的筆者,在面試官所施以的引導性壓力下,終於改變作風,坦誠地道出我不知道的,嘗試在他們面前將陌生知識與已知的知識理論與框架結合起來,令面試官們看到了我具備足夠的靈活彈性與可塑造性,最終把我取錄。
到牛津求學的經濟成本自然不低。為了降低對父母家庭的負擔,獲取錄後的我也曾經有過一股衝動,打算放棄到英倫求學,留在香港修讀大學(當時也收到了兩間香港頂尖大學的錄取,以及有條件的獎學金)。但父母寧願勒緊褲頭,也要支持我到牛津念書。想起來,若沒有他們的堅持,我的人生也許會很不一樣。同時,我獲得了由郭炳湘博士(Walter Kwok)與郭夫人(Wendy Kwok)──兩位對我恩重如山的善人──的全額資助與津貼,最終讓我得以完成本科教育。沒有郭氏獎學金,就沒有牛津黃裕舜。我還記得,郭博士離世前曾在一個飯局上說過,獎學金初衷乃是希望能為國家培育出願意服務國家、熱愛香港的年輕人才。我畢生都不會忘記他的宏大願景與高尚情懷。
二、 學在牛津:讓你無所遁形的導師制
在牛津唸本科,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經驗呢?說實話,即便是在國際學校修畢中學課程的我,最初也感到無比大的挑戰性。還記得正式開學前的一星期,為我們上一年級「入門政治課」(Introduction to Politics)的一位在牛津讀畢本科、碩士、博士的「星級導師」,將一篇足有三頁長度的書與期刊名單(Reading List)發了過來,然後再添加了一份「導讀」。導讀第一句便是,「You are not expected to read all of this.」(你毋須嘗試閱讀這裏的每一本書或期刊論文。),並建議我們「挑選」名單上「有用的」來讀讀看看,從而撰寫我們的一篇論文。但對於不習慣取捨或選擇的筆者來說,這根本是一個令人無比懊惱的超級難題。我糾結地反覆思索,到底應當如何才能選出「最好」的閱讀,讓我寫出「最好」的論文?結果當然是花了4天時間(包括本留作與父母暫別的星期天)去讀書、讀論文,讀讀讀到頭也懵了,才發現原來論文限期將至…
結果我第一篇論文,寫了足足有5頁A4紙有多──「嗯,寫得這麼長,總算有個交代!」。沾沾自喜的我走進了第一課導師課(tutorial),也即是牛津與劍橋最為馳名的教學制度基石……然而早已看了我論文的那「星級導師」,先是拋出了針對我論文立論的「五大駁論」,再提出了7個非常詳細的反例,讓我無比慚愧,頓時想找個洞去自我隱蔽起來。討論過程中,導師不斷地要求我和我的同堂夥伴相互「批判」我們的立論,結果在他的「循循善誘」下,我終於上了我在牛津的第一課。
「你以為你什麼都知道?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
當然,隨着我「牛津年資」漸長,我慢慢學會如何駕馭這個節奏快而步伐急的學習模式。每一周平均20到30本書或期刊論文閱讀清單中,三分之一是必讀、三分之一可以「快讀」,然後有三分之一是供你周末坐巴士或火車在英國到處「串門子」時順便讀讀。幾乎每一周都要撰寫的課堂論文(一個學期有八周,修讀2至3科不等,平均每科都要寫5到6篇論文,產量共可高達十多篇論文),需要你去提供鮮明的分析框架與鋪排、縝密地考慮駁論與反例,而不是嘩眾取寵的極端立論(有個別牛津畢業的人士似乎沒有領略到這一點,以為愈吸引眼球便愈好,結果語不驚人死不休,這行為有點太簡單,過度天真了)。導師邀請你向同學提出「友善建議」,不是要你說,「這實在太牛逼了!」等的客套話,而是要你提出針對性批判與積極建議,說少點沒建設性的假話。這些學習心得,看來也能被視為人生哲理名言。
導師制並不能取代全級或全群修讀某一科學生都要出席的「講座」。但大學也不會記下講座有誰人出席,誰人沒有出席。出席率與成績可說是毫無關聯(筆者自一年級之後,便再也沒有上過總是令我昏昏欲睡的早上講座)。而從這一點上,也能看到貫穿着牛津教學模式的,乃是教授與導師們皆常常強調的,學生們必須「當家作主」。學生,得要為自己撰寫的論文、為自己的學習、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任。面對着素質好壞參半的導師(不是說他們沒有學術含金量,而是有一些導師確實不適合教學生,包括在學界很著名的),我們必須依賴自身的紀律性與獨立覺悟,以及依靠同學之間的守望相助。在課堂上,同學們也許會唇槍舌劍,將對方的論點打到「落花流水」,爭辯至面紅耳赤。但在課堂外,好的導師與學生卻往往能打成一片,有些甚至成為畢生的師友。在牛津,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三、 長在牛津:幾許風雨的研究生旅程
在牛津所跨越的8年間,我也成長了不少。還記得我讀畢本科生之後,打算留在牛津修讀政治理論碩士。當時只有19歲,正在開始三年級的我,第一次申請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當時自以為是「辯論高手」的筆者,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心態與年少氣盛的態度,大剌剌地去面試,結果自然非常合理地落選。當年獲選的,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歷史學家,成熟穩重而正直勇敢,學術能力也超卓。充滿書呆子氣而只有有限實戰經驗的筆者,絕對相形見拙。落選獎學金後的我,卻並沒有放棄通過政治哲學去梳理及批判這世界不公不義之處的理想,並隨即獲牛津沃弗森學院(Wolfson College)錄取,成為研究碩士生(MPhil)。2018年,20歲的我開始了研究生之旅。
2018到2020年的我,經歷了三大轉變。第一,我本科時期所接觸到的哲學框架,大抵以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為主(即便學界對這類別名詞至今依然沒有很好的概觀定義,但相對於歐陸哲學(continental philosophy),分析哲學基本上較為看重以釐清概念、語言之間的聯繫與邏輯等為基本方法,從而剖析與解答包括倫理學(ethics)、元倫理學(meta-ethics)、形而上學(metaphysics)等領域中的難題)。研究碩士時,我有幸能跟牛津眾多資深的非分析哲學(non-analytic)名家學習,體會到引入文學、歷史學等「另類框架」去處理哲學難題的必要及可行性,也見證到歐陸哲學的魔力與開放性。
第二,曾相信真理愈辯愈明的我,發現「競爭性辯論」(competitive debating)世界本身的遊戲規則與所重視的東西,根本與現實生活之間存有着很大、很大的距離。「贏了辯論」,卻「輸了人心所向」,從實戰經驗中終於領略到這是什麼意思。受龍應台打動人心的文章啟發的我,曾幻想一切都可以理由與原因來說服他人,到頭來卻發現原來真理是那麼的模糊不清,更是難以正反論來涵蓋的。成為研究生後,我開始與更多的學門同僚在牛津內外的工作坊(workshops)與會議(conferences)切磋、交往,發現除了所謂的「反駁」以外,其實學者之間更需要的是「建議」與「修改」,支持與鼓勵。
第三,在一位前輩機緣巧合的介紹下,有幸獲《信報》郭老總Alice給予我機會,開始為這份歷史悠久的報章撰寫專欄。第一篇專欄刊登於2019年1月。如今風雨不改,每星期一面世的「政思故我在」,不知不覺也寫了接近四年半有多。把文章結集成書的第二本書《地緣風雲》也即將面世,也可說是我對這個時代的小小貢獻吧!
2019年。香港陷入一次前所未見的浩劫之中。在那些烽火連天的瘋狂歲月中,我更發現到原來書本知識,永遠都是那麼的有限,現實政治與生活,卻是那麼的複雜而難以簡單「二元分化」。有些表面形象未必討好的政客,在幕後嘗試調停與化解干戈,箇中付出之多,根本不為人道。那一年之夏,讓我更對改革的道義與價值產生堅定不移的信念。哪怕是冒着被網民起底、被各方勢力杯葛、被民粹媒體排斥、被曾經的好友割席與針對,我也堅持寫下去,因為我思,故我在。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詩經名句》說的。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這就是我所接受到的《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
2019年末,我決定要重新就着羅德獎學金拚一拚。我告訴自己,哪怕我這一次依然不成功,但我起碼對得住自己,展示出我應有的擔當。若我不再嘗試也許是最後一次機會的話,十年後的我,肯定會後悔。第二次申請過程中,我三番四次地反思了兩點。一,我當年失敗之處為何?二,這兩年走來,我學到了什麼,看到了什麼,依然不知的,又是什麼?想到了的答案,我嘗試以最為真摯而毫無保留的方法道出。
在完成了最後一輪面試(小組討論)後,在太古廣場某著名律師事務所中蹣跚地步行至地下某日本餐廳獨自食午飯。在食着反常地乏味的海膽刺身之時,接到了一通電話。深不可測而充滿智慧(也是兩年前親自通知我落選)的評審團主席聲音傳來,「Brian,你覺得你剛才表現如何?……恭喜你,哈哈!難道你對這結果感到驚訝嗎,羅德學人!」
那一刻,我在餐廳內幾近激動到流淚。
四、 傳承牛津:施教?試教?論教育的責任
旋即在2020年展開了政治博士(DPhil)生涯。當然,天氣不似預期。人算不如天算。開始這漫長征途之時,也是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之期。在《英倫歷險記》一文中我提到了,2020年3月份,我有幸及時從「淪陷」的英倫逃回非常安全的香港。抗疫經驗豐富的不少特區班子官員、擁有優秀操守與意識的港人、領導我們克服SARS與豬流感的專業醫護,他們都是我們在這一道沒有硝煙戰爭中的保命符。從疫情爆發到2021年末期之間,香港全城的抗疫記錄足以在全世界面前感到驕傲。當然,我也沒有因而耽誤學業。計劃書依然要寫。文獻依然要細讀。博士論文依然要準備。惟有遙距學習。
經歷了兩年有多留港的種種風雨及經歷,我在2022年春天毅然回到牛津,繼續走我一直都想走的學術路。我甚至執起了教鞭,搖身一變成為了當年曾覺得難以高攀,如今卻覺得難以駕馭的「導師」。第三學期,我向牛津本科二年級生授予「政治理論」(Theory of Politics)與「高階公義理論」(Advanced Paper in Theories of Justice)兩門課程,同時也獲聘為史丹福大學在牛津交換生課程的專責導師,負責教授「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n Politics)課程。跨到教學桌另一邊的我,終於得以就着教學的挑戰與收穫窺探究竟……
經常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成為最令我反感的「反面教材」,成為自己最討厭的人。作為老師,我有義務去聆聽我學生的訴求,去開解他們心扉,並開啟能讓他們自行持續學習的大門。有個別我曾遇到的老師,總是以為自己必然是對的,以「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姿態指指點點,搶佔道德高位,卻永遠不會就着自己的錯失向學生道歉,更迫使學生接受自己的橫蠻無理、自相矛盾。有見及此,我當時立下一個誓言,要求自己必須以同理心為先,以學生的心理與角度出發,作為鞭策自身教學模式的調整機制。若學生覺得我教得太淺的,必須為他們提供額外的調研途徑與方向。若學生認為我教得太深入的,則必須為他們提供入門所需的知識。
摸着石頭過河,確實不容易。其中一科,我第一堂便跟我的學生說,「我不要你們單純在這裏『學習人生觀』,我更要確保你掌握必須的技巧,能在終考中將你們分數從二級榮譽(上)提升至一級榮譽。若你們論文素質在這學期內沒有改善,我會當成是我的失敗!」
學生們課後跟我說,「你是我們第一位真的會教我們答題技巧與分析good與excellent論文之距離的導師,感謝你!」在此,我也衷心祝福我的學生,能在如今正在舉行得如火如荼的考試中,連連報捷!
也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在一個合適的崗位,將我這些年學會的融會貫通起來,為世界的共同未來出一分力。我的未來又會如何?耳邊響起張雨生老師高昂的磁性聲音:
「我知道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的過每一分鐘」
About the author
Brian Wong, 2015 Kwok Scholar, is pursuing the DPhil in Politic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s a Rhodes Scholar. They are the founding editor-in-chief of the Oxford Political Review. They are teaching undergraduates in modules on political theory and science at Oxford. Their book "Metamorphosis" i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in September 2021.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12 June 2023 in 政思故我在 by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