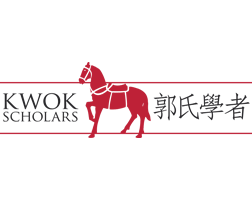18 April 2020
18 April 2020 

By Brian Wong
中間派有無未來 (下)
香港需要「真。改革」
香港需要改變,更需要改革。香港政治需要的新氣象並不可能是現存僵局的延伸,更不可能在現有的政壇渾水中出現新曙光。今期筆者想將過去兩週的討論劃上一個句號,專注探討香港今時今日需要的改革。再問一句,在如今政治環境如斯惡劣的情況下,香港人能夠做到什麼?
一、 三點現實
筆者認為有三點事實,任何香港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楚。
第一,香港有兩個,不是一個。
香港此城市由著看似南轅北轍的思想共同體所構成。
有一個思想共同體以香港作為中國文化、政治、及體制的一份子為依歸,認為任何在香港推行的政策必須符合國家利益及「政治正確」,以至在身分認同層面上,當中人士不單以自己身為中國人為驕傲,更對香港的本土身分抗拒及排斥,認為乃是代表著西方社會及「殖民主義」的殘留物。對於這些人來說,香港的價值觀乃是社會安穩、經濟發達、而政治層面的問題其實乃是物質主義追求的延伸,反映出香港既有資本壟斷主義所出產的次品。在此簡稱為「國家為主」之人。
另一個思想共同體則以香港作為價值觀、利益,以及身分想像的核心。請注意,這些人並不一定,也大部分其實抗拒港獨。他們深知道徹底的香港獨立並沒有可能性,但他們在推行、審視、衡量政策及法規時,自然是以香港作為一座城市及獨立政制為出發點,著重在西方國家較為普及化的民主法治、個人產權、自由等價值。他們視香港今日的局面為內地與香港政制衝突的結果,而有不少較為激進者甚至將此扣上陰謀論色彩的演繹。在此簡稱為「香港為主」之人。
須知道,這兩個共同體當中有不少重疊。「淺藍」的人士可能認為香港價值乃是值得捍衛,但必須透過與大陸有機結合才能真正地保存。「淺黃」的支持者有可能在週末自行北上深圳去消費購物、家人可能常常與國內親戚保持關係。甚至「真。建制」人士見到示威者在衝突中頭破血流、「深黃」看見內地人士被部分人士圍毆,都會感到悲憫,心中感到不安。理論上,這兩個共同體存在在一個光譜的兩端,而兩端之間是相同的。但現實是,光譜當中的流動正隨著過去香港十個月的政治運動所激烈減少。可塑性越來越低,而意識形態主導身分認同的現象越加激進。所謂的「中間」,如今無人問津。
第二,香港政治與國際政治,本質上確實息息相關。但未必對「香港為主」的人士有利。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美國建制政黨視香港為其「反攻」大陸的舞台及渠道之一,但實際上能夠投放於香港的資源,一來出於經濟上香港獨特關卡地位對美國重要性,二來因為「攻打中國」有太多太多其他的燃點可以發炮、三來特朗普決策飄忽不定,如今國難當頭仍在自救,所以對香港所謂的「援助」或「支援」根本只是聊勝於無。對於「國家為主」的人來說,支持祖國是理所當然的事實,因為這關鍵時代並不容納軟手軟腳之徒。
反之,以「香港為主」之士則面對一個根本性難題。當中央認為自己於香港進行任何讓步之時,也會被當作是對西方群國的一種妥協;當中央將對香港的方針與國際策略掛鉤,並對香港本地建制徹底失望時,這也意味著港人已經沒有可能再可以主宰自身政治前途。任你如何進行政治遊說,國際對香港添加的壓力越多,國家能夠保存面子而「妥協」的空間也就越少。中央過去一年來對香港政策的收緊,從北京的角度來說,是再正常不過。10年溫和的妥協你們不接受、14年佔中後換了政治格局你們也不接受、直至19年,還要在國家如臨大敵之時搞個大頭佛出來,這叫國家如何能夠接受你們的要求?而港人在立法會選舉前也自然不會「鬆章」,只見劍拔弩張。一拍兩散,不是夢。
第三,香港現存不少社會經濟問題,固然與政制缺憾有一定關聯,但更多的反映壟斷式資本主義及走歪的市場經濟,加上政府長年不作為,所遺下的爛攤子。
從今次疫情層面來說,特區政府比周邊不少政府做的來的為好。但基層人士「手停口停」、住在籠屋的居民所承受的煎熬、科技創業創業未半而中道擱置、醫療人手不足、民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些種種問題都是市民的燃眉之急。一個民選的政府未必一定會帶來解決方法,而將民主等同於民生及良民之政,不只是有違社會科學原則(註:確實有不少學術文章指出,國民平均收入與民主穩定有正面關係,但因果關係乃是前者維持後者,此乃是另話),更是忽略了民主本身的非結果性價值 (non-intrinsic value)。所以香港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姑勿論政治立場或黨派背景,去就著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不應,更不可拖延。
如果讀者讀完以上三點發覺不敢苟同,或認為筆者乃是無知天真,大可以省略接下來的內容。
二、 三條出路
所以香港現時有三條可能的「出路」。當中有兩條筆者認為是死路。
第一條,乃是「兩個香港」全面開戰,趨向愛爾蘭式內戰模式。反對政府者,不止於2020年立法會選舉爭取超過35席,更透過所獲得的大多數執意癱瘓議會運作。激進抗爭者所使用的暴力升級,在外國所進行的遊說繼續拓展及深化。泛民或本土派任何民生上的妥協將被視為「出賣選民」。香港墮入政制危機,而部分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也繼續硬碰硬,加強對香港反對派的砲轟,也將本來容忍或包含的溫和反對聲音拒於門外。香港軍事化、衝突恆常化、流血事件在疫情後捲土重來。兩三年後,一國兩制在堂而皇之的理由及雙方的「鷹派」敦促下提早結束。五年後,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全無。十年後,香港成為中國的二線城市,「北上廣深」下面來個香港,很漂亮。
第二條,乃是以「香港為主」的陣營放棄批評政府,突然全面「歸順」政府,成為建制的一員。有不少保守派認為,透過民生及福利政策,能夠達致這一步。這也許是因為「反對政府」的人放棄了香港,也許是因為建制能夠調動資源,故能導致大部分港人接受現有政府及管治。與此同時,泛民及本土等「反對派」所推崇的激進政治,在民生蓬勃發展,香港市面看似欣欣向榮下,只會淪為茶餘飯後的意識形態討論,城市充滿著「快活的空氣」。這條路,筆者認為,將會扼殺香港得天獨厚的人才及對香港未來抱有願景希望的年輕人。更重要的是,要香港走到這一步,根本是沒有可能:政治問題需要政治解決,政治解決需要一手硬,一手寬,要不然只會本末倒置。
第三條,也就是筆者多個月來認為香港必須走的一條路,便是港人必須認清楚,香港是中國一份子,更必然是中央所重視的政治地帶之一。撇除別有用心的陰謀論來說,中央並不希望或需要全面由上而下地接管香港,但對香港確實有兩大要求:第一,管治香港者必須不違反或推翻國家安全;第二,繼續維持香港與國家金融及經濟上的合作及融合。港人如果不想認清此現時,只會是自欺欺人。
可是在這兩大原則下,港人有必要,也有餘地,可以在可行的空間裡與中央坦蕩蕩地表達自己的訴求。民生的議題盡可能與政治糾紛切割(當然,前提的是反政府的政客有決心去這樣做)。政治議題必須是在一個摸索雙方「可改變底線」,及接納雙方「無可改變底線」的前提下進行討論。在普選及政改之外,有心人必須反思如何能夠促進及改變香港管治文化。在政改層面上,港人必需意會到,這半辯論、半遊說的進程必然未能是一帆風順,而無人敢寫包單證明此路可通。但如果香港要達至可行制度下的政治復甦及進步,就必須放下身段。當然,身段放下多少,底線放在哪裡,這是個人原則性問題,更是一個實用主義與意識形態主義之爭。但如將任何談判(如泛民10年的談判)等同於「投降」,這種焦土性思維只會將香港推向第一條路線的無底深淵。
三、 香港願景
我理想中的香港是如何?
在現有可行限制下,我認為香港必須推進協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促進符合自由意志主義的平等局面 (egalitarian libertarianism)、並與國際普世主義 (global cosmopolitanism) 接軌。
第一,香港有必要將「協商」思維融入管治當中。既然雙普選並不能在短期內落成,香港需要引進一個一、能夠動員市民的創意及自身獨立思維;二、促進地區市民對地區產生歸屬感;三、將反對聲音及多元意見直接灌屬於施政進程中;四、讓政見相異的「兩個香港」在政治制度重新找到共同點的一個多元化政治體制。有關協商民主的理論,可見貝斯提 (Joseph Bessette) 、哈貝馬斯 (Jurgen Habermas) 、米爾(David Miller)、陳家剛等人的著作,這些理論家本身對協商民主也有頗為不同的見解。實際點來說,定期舉行地區辯論大會、放權於區議會及區內素人進行對自己社區的改革重組、鼓勵官員走入民間或上網聽取民意、將「中策組」徹底改革並將所謂「黃營」或不同陣營及界別人士直接吸納入內,這些都是協商性思維的表象。更根本的是,一個沒有大多數選舉民主的香港,並不代表沒有任何民主。民主可以透過界別及代表之間在透明公開規矩下的協商、官員與市民之間的辯論、以至對政府行政架構的拓展及政治人才培訓,從而讓香港能夠在體制上與時並進。中央需要人才來治港,更需要一個能夠充分論證「一國兩制」行之可以有效的團隊。港人希望政府能夠「接地氣」,聽市民訴求。當中協商民主正能發揮關鍵作用。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假改革」,也有人會認為一個沒有約束力的政治體制沒有可能確保民生安穩、民眾得到保障。這些人的擔憂不無道理,但我堅信只要當權者可以放膽一試,在可以控制的範圍裡推進達到雙贏的「緩衝改革」,這未嘗不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第二,香港必須符合平等主義及自由意志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最基本要求。平等主義(機會平等 (opportunity egalitarianism) 或運氣平等主義 (luck egalitarianism))的出發點乃是人人,無論政見立場、性取向、族裔、宗教,皆可以獲得同樣的對待,而同等對待有可能意指同樣機會、又或是同樣能夠接觸優勢 (equal access to advantage)(詳見現代政哲一代宗師柯恩的著作Gerald Cohen)。接地氣點來說,無論你出生是一名富人或窮人、大陸人或香港本地人、伊斯蘭教或基督教,政府必須確保你都必須有向上流的機會。
另一邊廂,香港獨特的政治及歷史進程下,導致港人對自由及私有產權兩者都看得很重。我們必須認清楚一點,公民社會對自由的追求並不能單純地被歸納為「利益」(utility) 或平等 (equality) 層面,而這也正正是為何政府並不應該將稅率增價至30%(或經濟效益來的最高點),也是為何香港並不會或應該強逼富商「捐錢」給予慈善機構。可是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並不是萬能,而必須符合對以上平等主義的最低限度要求。香港需要一個持續而全面的安全網,讓最為「窮困」的人也能生活在一個有尊嚴及有社會向上流動機會的線上。與其追求無止境而只會「趕走資金」的政府干預,倒不如集中將香港最需要我們援助的人提升至一個舒適能夠自給自足地往上流的生活水平。同時,身為一座國際大都會,香港必須正視對少數人士的歧視及逼害,這也是國際社會對人權及民權的最低要求。
政府存在的功能並不是要將人民塑造成能夠迎合社會,而是應將社會打造成一個能夠符合各式各樣人民安居樂業之地。香港並不是人人皆會成為律師、醫生等所謂的「神科」,and that’s absolutely alright。如果一個香港人因為自己的取態及生活的追求而被香港非常單一化的經濟體系排斥在外,這不但有違基本的平等主義原則,更是有違社會大眾利益。只有一個「知人善用」而人人大致平等的社會,才能將社會利益最大化。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能確保人人生活水平都獲得提高 (詳見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最新的一書)。
第三,香港並不能摒棄自己作為國際中心的地位,更要放眼周邊地區,投放資源去鞏固自身軟實力。中央固然沒有原因去抗拒香港對自身軟實力的增長,而港人也同時能夠透過這「國際陣線」獲得文化、社會及經濟資本去促進自身發展。
筆者曾經說過,「新本土主義」需要的並不是固步自封的「向內收」,而需要香港人「往外走」。往外走並不代表只「回大陸」,或單純的「一路向西」,而是意味著港人能夠將自身獨特的價值觀及令人因而為傲的文化輸出,將我們的經濟及法律系統傳承於世界各地,再以香港為一個大本營。國際陣線的對頭人並不是中國內地,更不是中央 – 國際陣線的對家應該是在新型冠狀疫情下於外國抬頭的泛反華主義(也包括香港在內),更是西方各國內部出現的本土及反全球化主義。當全球化於世界各地皆受到嚴重衝擊時,香港得天獨厚的經濟及人文條件讓我們理應需要擔當更加重要的國際角色,而不是在如絲關鍵時候煽風點火。
四、 結語
香港今天,未必有明天。
香港如今已經去到一個水深火熱的地步。若任何人以為香港未來三年可以靠著「小修小補」政治,或者「繼續扮演常態」的手法去進行管治,這不但是天真,更是害了香港,將香港推到第一或第二路線上。香港現時身處水深火熱的危險邊緣,極度需要改變。
「排斥」激進、支持「溫和」、進行「妥協對話」,這些口號,大部分人都會識寫識講。
但是在「回歸正常」、「恢復穩定」、「止暴制亂」等氾濫的語句背後,又有多少人真正反思過,何謂正常、何謂穩定、還有便是,究竟香港今時今日走到這一步背後的結構性因素為何?當兩邊人的「正常」其實已經處於十分非正常的徹底撕裂下,其實恢復「正常」,又有何意?
所以香港不需要「中間派」。
香港需要「改革派」。
About the author
Brian YS Wong is an MPhil (political theory) candidate at Wolfson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current Rhodes Scholar-elect for Hong Kong in 2020.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18 April 2020 by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